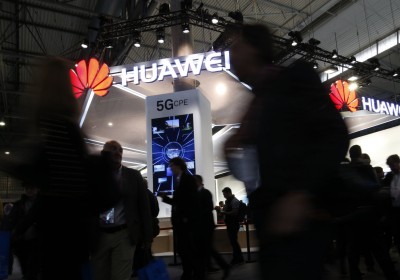遊覽一個城市,可以有不同方式,自駕、跟團甚至遊蕩。一些藝術家的選擇則較為另類,甚至可說是「踩界」的方式 —— 他們選擇「跟蹤」一個陌生人,秘密沿著其路線來走,說是由此能夠看到一個新的城市。
專欄作家 Debbie Kent 分享一次在異地的「跟蹤」經歷,在抵達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兩日後,她跟著一位穿粉紅色褲的男子,隨著他走到城市的郊區。過程中,Kent 有時不得不亦步亦趨地緊跟著他,但又不能跟得太緊。
「跟蹤陌生人」是塞爾維亞藝術家 Miloš Tomić 建立的另類旅遊方式。Kent 雖喜歡這個概念,但同時也感覺自己好像在做些不對勁的事。她當然不是想跟蹤偷窺那個陌生人,當陌生人離開公共空間,進入私人公寓後,Kent 也就立即離開了。
正如藝術家和作家 Phil Smith 所言,Kent 只是將探索城市的權力轉移到隨意選擇的人手上。Smith 自己也常將這項任務交給普利茅斯大學(University of Plymouth)的戲劇及表演系學生,視之為一項有價值的練習:「我們的想法是,你去探索這個空間,但有人為你作決定,這會令你的意願更中立。 (跟蹤的)意圖是,希望所跟蹤的人可以帶你進入以前沒有去過的地方。」
在沒有嚴格的法律定義下,「跟蹤」愛好者需要與目標保持距離以表尊重。Smith 給學生的規則之一,就是如果目標意識到被尾隨,就要立刻停止。「另一個規則是,他們不應該跟蹤任何會令他們感到不舒服、或者因他們的存在而感到不自在的人。」
藝術家追隨陌生人的想法有著悠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840 年由愛倫坡(Edgar Allan Poe)撰寫的「人群中的男人(The Man of the Crowd)」,敘述者在倫敦的街道,無特別理由地追趕一個神秘的陌生人。而 Smith「跟蹤」練習的靈感則來自概念藝術家 Vito Acconci,他 1969 年在紐約街頭拍攝的 Following Piece 定立了楷模:「每天我都會隨機挑選一個走在街上的人,我一直跟著,直到那個人進入我無法進入的私人場所(家中、辦公室等)。」
法國藝術家 Sophie Calle 在 1980 年的作品 Suite Vénitienne 更破格,她進入更私人及具侵略性的領域,記錄一名在聚會上遇到的男子在威尼斯的行蹤。在另一作品 The Detective 中,Calle 聘請一名私人偵探跟蹤她走過巴黎,然後將報告與照片一起發佈。這種手法越界到跟蹤、騷擾及侵犯私隱,Calle 就經常因為藝術,而故意玩弄及侵奪自己的生活,也因涉及道德界限而備受批評。

現時以跟蹤作為作品內容的藝術家都會說他們盡其所能保持距離,並保護目標的私隱。在中國南京大學教授的表演藝術家 Bill Aitchison 說:「不能引人注意,你不會想嚇到他人 —— 你是真會被抓住的。」
Aitchison 指,鑑於自己身高超過 6 呎,隱身是一個挑戰,但他已經駕馭了各種技巧:「可以留在最遠的距離,但你可能因過於小心就不見了那個人。」當快要被發現時,「找些事情做非常有用,你可以隨時查看手機,或假裝看電話。飲飲食食也是避免看起來可疑的好辦法。」
雖然驚險,但 Aitchison 說:「這既是了解人們,又是了解城市運作方式的一種方式。」他會選擇與自己截然不同的人,「例如在阿姆斯特丹,我開始跟著矮小的人或老年人。這樣做,你就會知道他們會去哪些地方,感受到他們如何使用這個城市。」
來自美國的組織 Walk Exchange,其聯合創辦人 Blake Morris 幾年前開始在紐約重建 Acconci 的 Following Piece。他說:「這令我聯想到我們收集地方數據的方式。你跟蹤周圍的人,以了解他們的日常路線。」他指出,現在的手機 GPS 無時無刻跟蹤著每個人,大數據已能描繪出人群移動的城市統計圖表。
俄羅斯藝術家 Alisa Oleva 亦會跟隨下班人士從地鐵站回家,探索莫斯科絕大多數工人居住的住宅區。Oleva 自己在同一個郊區長大,她說:「我不擔心侵犯人們的隱私,因為它與倫敦那些地方非常不同:你跟隨一個人走到一大片公寓,而不是私人大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