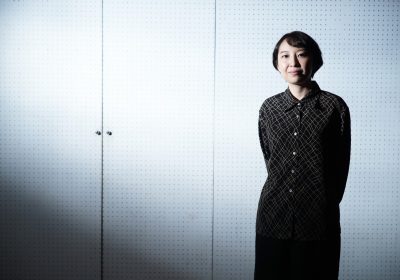近來有不少朋友重提「張愛玲當初為甚麼會離開中國」的舊題,有關這個她一生中最關鍵的抉擇之一,由於她本尊一貫報以曖昧和冷酷的態度,我們只能無限猜下去。
她離開的那個年月,可算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關鍵的轉捩點,對比她這樣一個寫通俗小說的女青年,許多比她飽讀詩書,大半生都在研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大知識分子都選擇留下,然後,就沒有了然後。
換言之,離開還是留下,和智商、學問、品格道德,沒有太大關係。好友說,這取決於審美的直覺,可以說是一個主因。
但審美的直覺從何而來呢?很值得探討。
一般來說,似乎女性比男性的直覺更為敏銳,據說這和人類進化的選擇有關係,就繁衍和保存下一代的使命而言,女性需要對於安全感有更好的判斷力。安全感本身和審美有直接關係,資源貧乏,缺少比較和選擇,環境破敗、骯髒,顯然無法令人產生安全感。因此城市女性應當比農村女性有更好的直覺。
但是張愛玲的直覺為何又比起一班男性知識分子,更為敏銳呢?可能關乎女性另一個比較顯著的特質,就是虛榮(vanity)。
諷刺虛榮(vanity)的文學作品多不勝數,但是,虛榮的作用有點像藥物,只能適度攝取。過度的虛榮,固然令人厭煩;完全沒有,則少了點人味,如果對人性的弱點有所寬容,斷不會以虛榮是甚麼嚴重的過失。西方文化對於虛榮是包容的,而且常以此自嘲,虛榮之心,可說是文明人皆有。
培養審美,不能太務實,太務實的時候,容易放棄原則,只求滿足功能,則女僕裝就不必在黑袍外再加一件白圍裙;同樣也不能太離地,否則容易沉浸在理想世界中,對現實產生虛無和幻滅的感覺,審美的直覺,取決於一點恰到好處的虛榮。
而張愛玲顯然是一個虛榮的女人,她特別喜歡服飾,尤其是擺弄「奇裝異服」,可惜當時上海的時裝資源選擇太少(雖說上海已經是中國資源最豐富的城市了),否則可能有機會成為另一個 Diana Vreeland。

虛榮的目的,或為充撐自信,或為吸引人,或單純為快樂,一定程度的虛榮可以有積極效應,尤其是女性對於精緻妝容,優雅服飾的癖好,樂見梳妝臺上香水、唇膏、粉撲的琳琅滿目,滿足各種感官的享受,此一虛榮的儀式,本身就是生活安全感的表達方式 —— 那些不屑於外表虛榮的人,可能就會另尋替代品,譬如高尚的名聲、動聽的口號、偉大的理想等等。
張愛玲的虛榮感,可能與看電影也有關。電影可說是決定現代城市審美觀的最主要因素,甚至有影響愛情觀的作用,明星販賣的是最直接的性魅力:外貌、體型、神氣、動靜,幾乎不需要內涵,是虛榮的全方位表達方式。批判外表虛榮,禁止直接表達性魅力的社會,怎麼能給人安全感呢?
當年許多文藝青年奔赴革命根據地延安,包括理想主義的美國記者,在他們眼裡,追星的膚淺、貪靚的虛榮,於革命宏圖而言,都十分可鄙;因此,他們看見黃土高坡、農民老鄉,只覺淳樸可親,而不會從資源貧瘠的角度來思考;看見革命家身上皺巴巴的棉衣棉褲,發黑的衣領和袖口,唯是這些不貪圖外表虛榮的大好青年,才兩眼發光,看見這些人可以抛開一切令生活變得輕鬆的奢侈資源,譬如自來水和抽水馬桶,堅持為理想奮鬥,而不是像西方中產階級那般平庸墮落,簡直是人類之光了。
如果那幾個美國記者,平時愛喝威士忌,穿的是巴黎的絲襪,只是膚淺地迷戀 Clark Gable 或者 Cary Grant,又怎麼會山長水遠去中國大西北朝聖呢?正如特首林鄭,如果她在讀書的時候,也很貪慕外表的虛榮,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打扮自己身上,日後便不會通過「投身社工」、「關心貧弱」來證實自己高尚;如果她看男人的眼光,也多幾分虛榮,多看幾個男明星,就不會隨便把甚麼政治領袖當作男神了,對吧?
張愛玲當年只有 30 歲出頭,又不是清心寡欲的修女,對於生活和男人,總得要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多想一想吧。
有些想法錯得如此離譜,只有非常聰明的人才會相信。
There are some ideas so wrong that only a very intelligent person could believe in them.
真的,不需要有太高深的智慧,不需要太多理性分析的理由,只要有一點小小的虛榮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