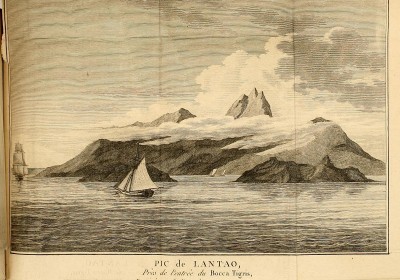港版國安法對電影進行嚴格審查,叫很多電影人無所適從。環顧全球,政治審查其實從不罕見,但無數電影人仍然堅持不懈,在縫隙間繼續用光影說話,伊朗電影人可說是佼佼者。在嚴苛的政治宗教審查機制下,有人運用有限空間發展別樹一格的電影語言,亦有人無懼刑責堅持拍攝禁片,為伊朗電影在世界爭得一席之地。
在伊朗革命前的沙王獨裁年代,反政府電影已經被禁放映,1979 年革命後上台的伊斯蘭政權,不但加強政治審查,新成立的「伊朗文化與伊斯蘭指導部」(MCIG)還加設多重審查關卡,確保過濾所有政治和色情內容,阻止西方文化價值滲透。部分著名影星被終身禁演,無數電影製作人與演員也相繼流亡海外,不少累積的電影技術和製作經驗失傳,加上政局不穩而投資中斷,令革命初年電影業幾乎癱瘓。
直到 1980 年代末政局漸趨穩定,電影人才開始嘗試在有限空間下創作。電影研究學者 Rosa Holman 分析,由於資金短缺,初時導演經常起用非專業演員,依賴戶外拍攝,不用燈光器材,而且經常以兒童擔當主角,背後關乎到道德審查考慮 —— 政府對描寫成年男女關係有嚴格規定,反而以兒童為主角可爭取更大創作自由。
兒童在伊朗電影中於是有了矛盾的定位,一方面他們是自由象徵,不受政權嚴格道德規範,另一方面導演又想借助他們說出成人世界的困境,結果故事往往富有寓言色彩,兒童的現實與內心掙扎通常隱喻更宏大的社會政治議題。導演馬吉迪(Majid Majidi)代表作「小鞋子」(Children of Heaven,1997)和「天堂的顏色」(The Colour of Paradise,1999)是典型例子,通常講述年輕的兄弟姐妹如何合力應對父母的嚴格要求。
迴避審查的詩意寫實主義
除此以外,伊朗電影還有濃厚的寫實傳統,始自 1968 年導演 Daryush Mehrjui 作品「牛」(The Cow)。此傳統在革命期間中斷,後來得到伊朗電影大師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繼承,再以「詩意寫實主義」(Poetic Realism)風格發揚光大,代表作「櫻桃的滋味」(Taste of Cherry,1997)更為他贏得康城影展金棕櫚獎,從此確立其國際地位。
在波斯文化生活中,詩比小說擁有更深厚傳統,基阿魯斯達米形容,伊朗人習慣在談話中引用詩句,這不限於知識分子和詩人,即使目不識丁也會背誦詩句來表達感受,令詩成為全民共通的語言。但影評人 Kaleem Aftab 提醒,電影的詩意運用其實也關乎審查制度 —— 無法提出直接的政治批判,電影人傾向透過詩性的昇華,在威權陰霾下探討人生價值與故事。
當然伊朗電影不只得單一面向,如今發展亦更為多樣化。「伊朗式分居」(A Separation,2011)和「伊朗式遷居」(The Salesman,2016)先後贏得奧斯卡頒獎禮最佳外語片,其導演法哈蒂(Asghar Farhadi)更三度奪得金球獎,標誌著近年伊朗電影成就,但不要忽視在時鬆時緊的審查機制下,依然有電影人不甘於規避敏感議題,不斷挑戰紅線而入獄。
伊朗新浪潮導演帕納希(Jafar Panahi)多次無視禁令拍攝,又公開參與反政府示威,2010 年被判入獄 6 年、不得拍攝電影 20 年,但他未有就此噤聲,被改判軟禁後繼續冒險創作,譬如只能在海外放映的得獎作品「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2015)。另一位知名導演拉穌羅夫(Mohammad Rasoulof)則秘密拍攝作品「惡與他們的距離」(There Is No Evil,2020),正面探討伊朗軍人執行死刑的道德兩難,贏得柏林影展金熊獎,拉穌羅夫本人卻被禁止離境,一個月後鋃鐺入獄。
無論是模糊紀實與虛構的詩性藝術手法、還是無視禁令的直接政治批判,伊朗電影人未有輕言放棄,伊朗電影不但未死,還在政治壓力下發展出獨一無二的藝術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