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個多月的時間裡,死亡、暴力與香港這國際城市愈走愈近。美籍作家 Dave Grossman 的經典作品「論殺戮(On Killing)」,系統地探討人類的殺戮行為,其中一章仔細分析與殺戮如影隨形的「暴行」。Grossman 在書中以「針對非戰鬥員的殺戮行為」定義「暴行」,以這標準或不完全適合於香港套用,但作者對施暴者的分析,對了解其心理、邏輯,值得時人借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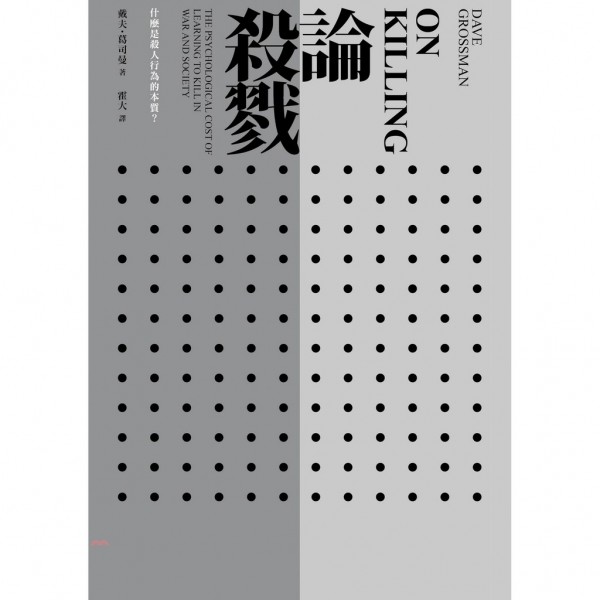
不了解暴行,就無法了解戰爭。作者指,暴行雖然可恥、邪惡,但非漫無目的,背後自有其利益考慮。要對抗暴行,必須先行理解其扭曲的邏輯運作。暴行最顯而易見帶來的利益是,能輕易使人心生畏懼,所製造的恐怖與殘忍能令敵人逃走及躲藏,消磨敵人意志,繼而將反抗瓦解。尤其是,一旦政府、軍隊以制度化手段實施暴行政策,施暴會更為暢順。其次,暴行亦能令不是置身現場的旁觀者心生疑惑,因為人不容易相信自己與惡的距離僅得一步之遙。而且暴行亦使人產生厭惡感,日常的道德與教育令人自我欺騙,寧願其從不存在,否認暴行與人類抗拒殺人的心理互為表裡。就如二戰時的德國,多數人也不敢相信集中營的惡行。
暴行的實行,依賴的不是鄂蘭提倡的「平庸的罪惡」,而是群體連結的行為。在威權體制下,領導人只要確認下屬參與暴行,就能扼殺下屬與敵人和解的可能,將下屬變成暴行的執行者,陷入當中的邏輯和罪行之間,要割席也殊不容易。
每一名主動或被動參與暴行的執行者,均面臨兩難的問題。一是屈從強大的暴行指揮者,以暴行論證自身於道德、社會、文化的優越,確信受害者死有餘辜。以曱甴等仇恨言論貶損對方、或期望自身行為受社會認同,就是這種心理的體現。一是勇於抵抗國家、權威的壓力,但同時可能面臨同袍的杯葛,甚者更可能被處以與受害者相同的懲罰。暴行將指揮者與執行者連結,只有獲得最後勝利,兩者才能不必為自身罪行負責,不必面對清算。
Grossman 認為,人類傾向高估自身的抗壓能力,每個人都以為自己不會成為暴行的執行者,在指令下達的關鍵時刻,能抵抗命令、群眾壓力,向罪惡說不。只是基於群體寬恕與同儕壓力,調轉槍頭的情況微乎其微。何謂同儕壓力,已是人所共知,不必多言。群體寬恕指的是,暴行的責任分散問題。指揮者因假手於人而不必面對良心責難,以至承受相關責任。執行者則普遍認為指揮者需為暴行負責,而執行暴行時在場的同袍及旁觀者也有參與其中,在群體當中能夠圍爐取暖,獲得寬恕。在群體寬恕與同儕壓力下,幾乎已能達到強迫個體參與暴行的效果。
正義每每姗姗來遲,暴行或許會令執行者日後出現創傷後遺,在事過境遷後面臨良心的責備,但這實與祈求天譴一樣軟弱無力,也救不了因暴行而喪失的生命。打壓愈大,反抗愈大。暴行肆虐,會迫使人群起反抗,盡力抵擋恐懼,為推倒暴政的高牆燃起星星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