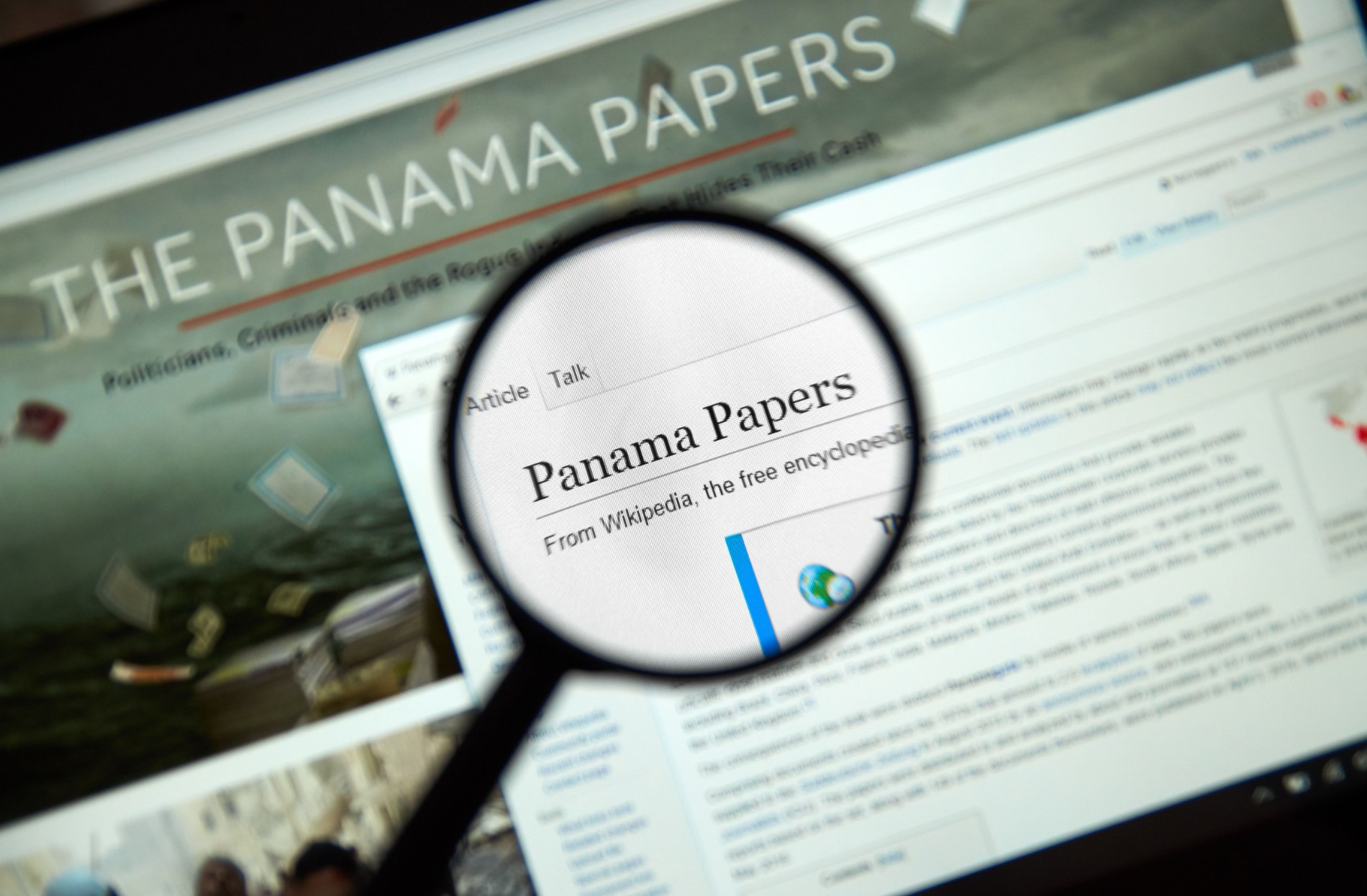
有說金魚腦袋記不住 15 分鐘前的東西,香港人也經常被批評善忘,去年發生的事,今天已經沒多少能記得住。近幾個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上網兩天已經搞不懂事情發展,更遑論上月之事。
這種健忘不能完全怪責香港人,在今時今日的情報環境,很難要求現代人記清生活中所有事物。在一人擁有一部手機的年代,自拍可以是所有經歷的證明,「記錄」遠比「記憶」重要,甚至前者取代了後者,成為生活經驗的核心。另外一個原因是情報資訊爆發性增加,深入生活每一細節,超過了人類大腦能夠處理的分量。當你還在咀嚼剛出現在熒幕的影像,系統已經把它換成下一幅。
如果是以前的鄉下務農社會,外人入村已經是新聞;但國際化城市裡,包括資本、風景以及居民,都處於流動的狀態,事物的誕生與消亡是每天的日常。要求個人能夠記憶並處理這種世界的脈絡,是不切實際的,所以我們需要 Database 與 Archive,將人腦無法處理與記憶的部分,交給媒體科技 —— 外在的記憶裝置。
香港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一直主張應該成立檔案法,阻止政府胡亂丟掉記錄文件,但直到今天,香港的檔案法仍未遙遙無期。歐美大國早在上世紀初已經建立了有關法律,世界大部分已發展國家亦在 80 年代開始,注意到資料庫及其電子化的重要性。
建立一個資料庫,並非單純把檔案資料全部丟進去就完成,還需要將資料整理分類、妥善儲存以及公開存取。而所謂的「公開」,也不單止將有關的資料放出來,還有其他條件,例如閱覽權的開放性、資訊平台的結構、資訊的可視化基準等等。
公開不僅僅等於開放資料,幾年前的「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是一個好例子。2015 年,「南德意志報」的記者從匿名洩密者手中獲得 2.6TB 的文件,需要近 80 個國家與地區的 107 個媒體組織協助,用 1 年的時間才初步整理好。
「南德意志報」沒有一口氣把所有文件上載到維基解密之類的網站,除了因為裡面包含非公眾人物與非違法的內容,也因為文件數量過分龐大。縱使將所有文件上載,一般人也很難找到有價值的部分,所以整理分類對資料開放來說是必要工序。讓人在數以億計的文件檔中尋找其中一個,等同在海灘中找一粒沙,這種公開與不公開沒有分別。
存在並不代表被認知,反而應該倒過來說,所謂存在即被認知。所以要確保香港人記得某些事,例如在 3 年後的今天,大家仍記得 2019 年 7 月 21 日的元朗發生甚麼事,依靠的不應該只是我們的腦袋,可能是一本還未出版的書、一個資訊整合網站、哪怕只是一條 Time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