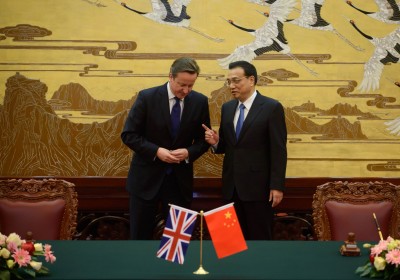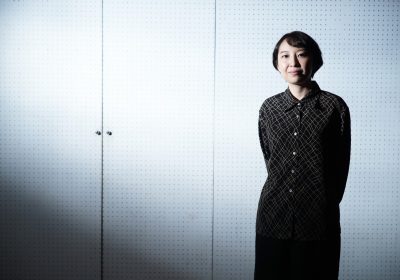在某些獨裁國家,無論政府如何貪污舞弊,軍隊如何屠殺人民,貧富如何懸殊,人民連上網的自由都沒有,依然會有一群真心擁戴政府的人。有學者曾經用父權崇拜來解釋背後原因,同時,有學者用為人熟悉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一個本來形容受害者對加害者建立情感聯結的心理現象,來解釋支持者對獨裁者的情意結。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源於 1973 年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宗銀行劫案,兩名悍匪打劫事敗,被警方重重包圍,他們於是挾持了 4 名銀行職員頑抗,歷時 6 天。可是,那幾名人質事後不單沒有憎恨劫匪,還表現同情。事後,精神分析學家 Nils Bejerot 就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形容受害人的心理反應。另一個經典例子是美國報業家族太子女 Patty Hearst,1974 年被激進左翼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綁架後,決定加入對方,最終於 1975 年落網。除了綁架,一些家暴、亂倫、強迫賣淫等案件,施害者和受害者一旦建立緊密關係,受害人就可能會出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創傷學始祖 Frank Ochberg 解釋了整個心理反應。在案件發生時,受害人會極度恐慌,認為自己大難將至。然後,下一步會經歷幼兒化(infantilisation)的過程,施害者會掌控受害人日常所需,令他們變到像小孩一樣,飲食、說話、如廁,都要得到施害者允許,而施害者微小的善意,例如給予食物,都會被受害人視為極大的恩賜。慢慢地,受害人會忘記自己是被施害者置於險境,反而對他們產生正面的情感,例如認同、服從、同情,甚至愛慕,認為施害者對他們自身生存不可或缺,而這也是一種自我防衛機制,令自己掩蓋創傷。
有政治學家就借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從集體心理學角度解釋為何一些人會擁護獨裁政府。例如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博士 Brahim Barhoun 就指出,獨裁者掌管了人們基本的生存需要,例如食水和人身安全,甚至大眾的生殺大權。有些獨裁者會展現出家長式的一面,口裡全是為人民福祉著想,而一些人也會因為這些「恩惠」而慢慢為獨裁者開脫,甚至產生同情、依賴,乃至崇拜的感覺。
Barhoun 和另一位時事分析員 Cord Jefferson 都以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為例,他獨裁統治埃及 30 年,任內被指殘暴鎮壓示威者,但到法院初審那天,大批民眾聚集堅稱他是清白;當得悉穆巴拉克被判處終身監禁,很多人更聲淚俱下;後來他保釋出獄候審,大批民眾又歡呼喝采,彷彿忘記埃及 30 年的貧困與不公是誰一手造成。秘魯政治學家 Alvaro Vargas Llosa 亦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形容查韋斯年代的委內瑞拉,指儘管政府獨裁,而且貪污和毒品問題嚴重,但查韋斯的強人形象令不少人產生依戀。德國政治學家 Andreas Heinemann-Grüder 也指出,一些俄羅斯地方精英也像患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政府就像劫匪,而他們就一邊給贖金,一邊對政府予以同情。
渥太華大學政治學教授 Stephen Brown 在政治學期刊 Democratization 撰文發表研究,他發現這種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不單止會發生在國民和國家之間,他深入訪問 70 名由西方國家派駐肯雅、馬拉維和盧旺達,處理捐款援助的職員,發現部分人長期生活在獨裁國度,會出現過度識別(over-identification)的情況,明明是監察者,卻會從獨裁者角度思考問題,他們不單會自我感覺良好,更會變得認同當地的獨裁者,甚至為他們說詞,認同他們的管治能穩定社會。
不過,開羅美國大學心理學家 Hani Henry 就認為,除了要解釋獨裁者支持者的心理,還有很多其他文化因素,例如埃及人本來就擁護一些集體主義價值。Jefferson 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分析埃及的時候也指出,其實有些「政府支持者」只是單純收了錢,是政府動員來製造聲勢,心理學分析只是其中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