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等身的意大利小說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離開人世 38 年,至今仍有作品未曾翻譯成中文,包括最新出版的英譯散文集 The Written World And The Unwritten World。在書中,卡爾維諾以遊走文字與非文字世界作為比喻,講述自身寫作心路歷程,更分享訓練洞察力的秘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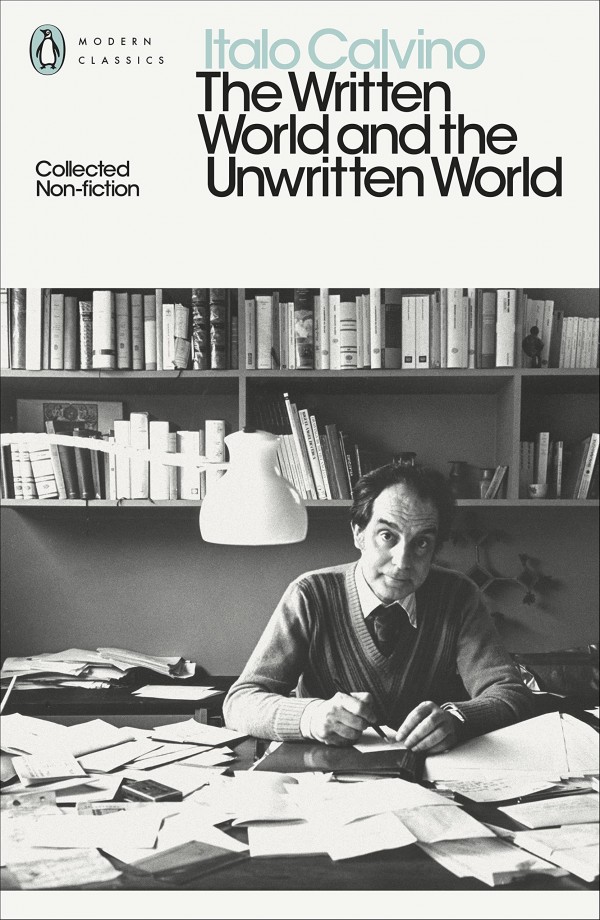
卡爾維諾在 1983 年發表的文章分享,年輕時曾經以為,書本世界與真實世界可以互相照耀、互補不足,但長大才發現兩者的落差。在書本世界裡,每字每句都有既定規律、可以理解,令我們得以組織看法,不論真與假、對與錯、愉快與不愉快。閱讀的經驗有始有終,一切不會越過書頁的邊界,為我們帶來一切盡在掌握的幻覺。
相反,每次面對三度空間、以五感體驗、居住在有數十億人口的真實世界,卡爾維諾都感覺「有如重複經歷出生的創傷」。當中有無數超出我們可理解的狀況,使人不知所措、驚訝、疑惑,在錯綜複雜的體驗中,我們很難把現實梳理成可理解的形狀。即使經驗再豐厚,我們都很難預測任何事情,更遑論是全體人類未來。
縱然書本世界是舒適圈,但卡爾維諾認為,依然有必要朝著書本以外的未知冒險,原因在於作家的職責 —— 讀者都期望,作家能夠環顧四周,在萬變的混沌之中,洞察出多少的規律,然後回到書桌上,把這些吉光片羽一一記下。
被文字殖民的外部世界
不過,要如實經驗外部世界,不是放低書本般容易。上世紀的法國後結構主義便嘗試說明,我們不可能逃離語言束縛,甚至不存在語言以外的世界。卡爾維諾亦坦言,我們的世界大多經文字組織而成,覆蓋著一層厚厚的話語外殼。
儘管哲學上的現象學方法、文學上的間離效果同樣承諾,可打破文字和概念的屏障,叫我們如初見般重新經驗世界。但卡爾維諾提醒,我們眼睛依然無法擺脫閱讀的文化訓練,其中牽涉一套抽象思維,叫我們不自覺把事物分類和標記,重新排列出意義,發現其中的規律、差異、重複、歧異。
部分作家另闢蹊徑,如美國詩人龐德(Ezra Pound)、愛爾蘭作家喬伊斯(James Joyce)和意大利詩人嘉達(Carlo Emilio Gadda),都嘗試模仿日常世界的語言特性,像馬賽克般拼貼文字。卡爾維諾卻認為,這種模仿不是作家的真正挑戰,反而應該利用看似通透的文字,重構我們錯綜複雜的處境,就像卡夫卡的寫作般。
透過凝視重新經驗世界
要達到應有的洞察能力,卡爾維諾建議最簡單的辦法,是把注意力聚焦在最平凡、最熟悉的單一事物上,然後進行極細緻描寫,就像凝視全宇宙最新、最有趣的事物般。這是從現代詩創作所汲取的靈感,即把全副注意力、對細節的熱愛,全都投放在與人類形象相去甚遠的事物身上。
在法國,散文家龐日(Francis Ponge)為不起眼事物寫散文詩開始,如一塊肥皂、一塊煤炭等,「物自體」(Thing in itself)便成為了文學課題,在卡繆和沙特寫作下得以延續,後來更有羅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為一片蕃茄創作,德國作家漢德克(Peter Handke)亦實驗以地景創作小說。
卡爾維諾重視這些練習,是基於創作小說「帕洛瑪先生」(Palomar)時的挫敗經歷。他發現自己大篇幅描寫事物,但都無法轉化成故事,每個角色都只能根據自己所見來思考,對其他任何想法都一概懷疑。卡爾維諾最終發覺,問題出於自己欠缺「觀察家」的技藝,從未全神貫注在某事某物身上,於是他決定先重新學習觀察,然後再執筆描寫。
以克服不可能為寫作動力
洞悉自身的不足,從來不是卡爾維諾眼中的寫作障礙,反而是動力來源。「每當我確信某類型的書,完全不符合我的性情、超乎我的能力,我便會坐在桌前,開始寫作。」其名著「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If on a winter’s night a traveler)正是如此誕生,一度是卡爾維諾眼中「自己永遠不會寫的小說類型」。
他還透露自己的另一個寫作大計,是以五感創作小說,偏偏自己的五感都不夠靈敏,要努力學習掌握一系列感覺的細微差異,坦言不肯定最後能否成功。多年以後,我們知道這部五感小說,正是他未完成的遺作「在美洲虎太陽下」(Under the Jaguar Sun),最終只有嗅覺、味覺和聽覺的故事完稿。
這種克服困難的自我訓練,與其說是為了寫書,不如說是不斷完善自身,卡爾維諾認為,這是所有人應有的目標。從某意義上說,作家就是不斷向未知出發、寫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偉大作家更能夠保持對未知的渴求,讓非文字世界能夠通過作家之手顯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