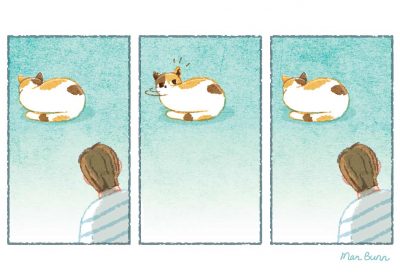From this day to the ending of the world,
But we in it shall be remember’d;
We few, we happy few, we band of brothers;
For he today that shed his blood with me
Shall be my brother.”
從今天直到世界末日,永遠不會隨便過去,
而行動在這個節日裡的我們也永不會被人們忘記。
我們,是少數幾個人,幸運的少數幾個人,
我們,是一支兄弟的隊伍 ——
因為,今天他跟我一起流著血,他就是我的好兄弟;
對於戲劇家而言,壞人永遠是上好的素材,暴君、昏君、荒淫無道、殘忍無情、自大傲慢而最後自尋死路,都是賣座的保證,如何寫一個好的君主,才是莫大的挑戰。
在莎士比亞筆下,只有亨利五世是罕有的好國王,原因也就顯而易見了。
亨利五世上場之前,坎特伯雷大主教就對他作了評價,以便觀眾有所心理準備:
憑他年輕時的那份荒唐,誰又能想到啊。他的父王才斷了氣,他那份野性彷彿也就遭了難,跟著死去;對,就在這時候,「智慧」,真像天使降臨,舉起鞭子,把犯罪的亞當驅逐出了他的心房;
如此本質的轉變如何能令人信服?大主教接下來便說出了觀眾的疑惑:
這可真是稀奇啊,怎麼他會學習得那麼多;他走的明明是條浮而不實的道路,他所親近的都是那些不學無術的淺薄之徒,他的時間儘是在聲色犬馬裡消磨;從來沒人發現他手裡拿著一本書,或是從嘈雜的場所,從三教九流的人群中退出身來靜一靜心。
擺在亨利面前的,有好幾個麻煩:首先是一條陳年議案,如果通過的話,教會將損失一大筆土地和財產;然後是法國反對亨利繼承他的家族金雀花王朝在法國的一部分領土;一旦他與法國翻臉,還要防範後院失火,因為「每逢我的曾祖父進兵法蘭西,蘇格蘭的全部人馬沒有一次不是浩浩蕩蕩,像潮水湧向缺口一樣乘虛而入」。
同樣是出兵打仗,亨利似乎沒有遭到強烈的反對聲音,即使有,他也沒有追究怪罪,儘管左右都認為這樣擾亂軍心的人,應該予以嚴懲,但是亨利堅持「還是放慈悲一些吧」,「要是人一時糊塗,犯下了小小過失,我們尚且不肯瞇著眼睛只裝不看見;那麼,一旦那用盡心計、深思熟慮的一等罪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我們的眼睛該睜得多大呢?」
這段自白,其實是為了鋪墊,因為亨利手下三個大貴族,與法國私自和談,計劃謀殺亨利,他們的陰謀及時敗露,亨利認為這是出征之前的祥兆。
為了襯托亨利得到民心擁戴,在亨利處決三個叛國賊之後,緊接是倫敦街頭一對經營客棧的夫婦正在道別,鄰里之間甚至還寒暄說笑了幾句,明知自己有戰死沙場的風險,但身為丈夫的還是擺出一副從容的樣子,原文的「像螞蝗一樣把血喝個痛快」,和「笑談渴飲匈奴血」幾無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齣名副其實的「愛國宣傳劇」中,作者又借用法國國王、太子、元帥的交談,來側寫亨利的形象,他們都沒有直接和亨利打過交道,但法國國王得出一個非常理智的結論,「他的祖先曾經拿我們當做一塊肥肉,曾經踏遍了我們的土地,而他,就是這些血腥的侵略者的後代」,因此絕不能輕敵。
封建貴族的戰爭,講究先禮後兵,在正式開戰之前,亨利派遣使節通知法國,要求法國國王交出王冠,讓給他這個名正言順的繼承人,同時附上一本皇室的宗譜作為法理依據。但是接下來真的上了戰場,就是鋪天蓋地的血腥和混亂。
和當今荷里活的導演一樣,在戰爭的大場面之中,作者把視角轉移到小人物身上,上一幕在倫敦街頭準備參戰的兩個小兵,此時躺在泥濘之中交談,客棧老闆為自己打氣:「上帝的子民倒地而死,手拿寶劍和盾牌,沙場上血流如海,博取那千秋萬歲的英名。」但是他身邊的年輕人卻老實承認:「但願我是在倫敦的酒店裡!我願意拿我一世的『英名』來跟一壺酒和眼前的安全交換。」
亨利在陣前慷慨陳詞,激勵軍心,本文的引言即出自這段著名的演說(St Crispin’s Day speech),而「兄弟連」(Band of Brothers)之說,也是出於此,挪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巧的是,地點也是諾曼底)也毫不違和。
莎士比亞身為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並不在於這些口若懸河煽動人心的文字,而是在於他能設身想像士兵的處境,尤其是他們背後還有軍官抽出刀尖在督戰,而且一些低級軍官也是其身不正:懦弱、醉酒、偷竊,「丟盡了男子漢的臉」,連小兵也看不起他們。而莎士比亞在這裡諷刺的對象,都是英軍。
而這場大戰就是英法百年戰爭中最著名的一場:阿金科特戰役(Battle of Agincourt)。
阿金科特戰役之所以在英國歷史上世代傳頌,原因有三:一是英軍以少勝多,二是武器和軍隊的改進(阿金科特戰役前,英軍中 80% 是步兵,20% 是弓箭手;但戰後比例顛倒,弓箭手大增);三是傷亡人數低,而法國在這次戰役中,喪失了大量高級貴族和軍官。
雖然寫作的目的是為亨利五世歌功頌德,但是作者並沒有貶低敵軍和敵國,反而加了一筆英軍將領劫掠法國教堂的小插曲,遭到軍法處決,亨利還補充道:
我曾經曉喻全軍,英國軍隊行經法蘭西的村子,不准強取豪奪,除非照價付錢,不准妄動秋毫;不准出言不遜,侮辱法國人民;要知道,在「仁厚」和「殘暴」爭奪王業的時候,總是那和顏悅色的「仁厚」最先把它贏到手。
然而這番話放到工業化和民族主義興起的時代,顯然就行不通了;再到今日媒體的無孔不入,輿論和宣傳開闢了新的戰場,孰為仁厚,孰為殘暴,也是任由人說,往往愈是有底線的一方,愈是容易被綁手綁腳。
仁厚戰勝殘暴,文明戰勝野蠻,這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理想,莎士比亞不憚於暴露英軍士兵的過錯和罪行,因為這樣並不會有損於阿金科特大捷的榮耀,人非聖賢,即使亨利也不例外。而亨利身為一位符合文藝復興標準的明君,最重要的條件,在第一幕裡已經有解釋:
我並不是甚麼暴君,而是一個基督徒國王,一切無常的喜怒都為理性所控制 —— 就像那不法的歹徒被囚禁在我們的獄中。
信仰的約束、理性的克制,這樣的特質,不得不說,也將預示後來王權受到的限制,和最終的退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