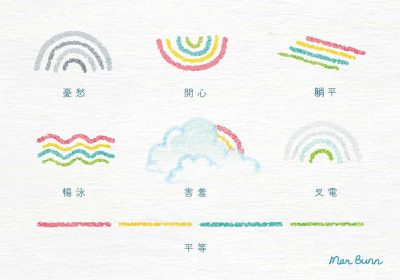Yea, but how if honor prick me off when I come on?
How then? Can honor set to a leg? No.
Or an arm? No. Or take away the grief of a wound? No.
Honor hath no skill in surgery, then? No.
What is honor? A word.
What is in that word “honor”? What is that “honor”? Air.
A trim reckoning.
Who hath it? He that died o’ Wednesday.
Doth he feel it? No. Doth he hear it? No.
‘Tis insensible, then? Yea, to the dead.
But will it not live with the living? No.
Why? Detraction will not suffer it.
(可是假如當我上前的時候,榮譽把我報銷了呢?
那便怎麼樣?榮譽能夠替我重裝一條腿嗎?不。
重裝一條手臂嗎?不。
解除一個傷口的痛楚嗎?不。
那麼榮譽一點不懂得外科醫術嗎?不懂。
榮譽是個甚麼東西?兩個字。
那兩個字又是甚麼?空氣。
好聰明的算計!誰得到榮譽?禮拜三死去的人。
他感覺到榮譽嗎?沒有。
他聽見榮譽沒有?不,
那麼榮譽是不能感覺的嗎?嗯,對於死人是不能感覺的。
可是它不會和活著的人生存在一起嗎?不。
為甚麼?譏笑和毀謗不會容許它的存在。)
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中,大多數角色是歷史真實人物,偏偏有一個家喻戶曉的角色純屬虛構,但因為活靈活現,很容易誤以為真實存在過,便是「亨利四世」的靈魂人物福斯塔夫(Falstaff)。
然而,福斯塔夫不但不是一個英雄,反而是一個大腹便便,好酒貪歡,信口雌黃,「無賴的胖漢」。
王子哈爾(未來的亨利五世)一出場,就把福斯塔夫的底細抖了出來:
你只知道喝好酒,吃飽了晚餐把鈕釦鬆開,一過中午就躺在長椅子上打鼾;你讓油脂蒙住了心,所以才會忘記甚麼是你應該問的問題。見甚麼鬼你要問起時候來?除非每一點鐘是一杯白葡萄酒,每一分鐘是一隻閹雞,時鐘是鴇婦們的舌頭,日晷是妓院前的招牌。
此時此刻的福斯塔夫,早已失去了曾經為國王戰鬥的鬥志,混跡鄉間,幹起偷盜的營生,甚至為自己辯白:「哈爾,這是我的職業呢,哈爾;一個人為他的職業而工作,難道也是罪惡嗎?」
令人疑惑的是,王子怎麼會和這樣的人為伍?劇中的他為自己辯白:「當我拋棄這種放蕩的行為…… 我將要推翻人們錯誤的成見,證明我自身的價值遠在平日的言行之上;正像明晃晃的金銀放在陰暗的底面上一樣,我的改變由我往日的過失所襯托,將要格外耀人眼目,格外容易博取國人的好感。我要利用我的放蕩的行為,作為一種手段,在人們意料不及的時候一反我的舊轍。」
但是,王子就是後來的亨利五世,莎士比亞最推崇的理想君王,是不是因為曾有這樣一段放蕩歲月,有這樣坦蕩蕩的損友,才使他成為平易務實的統治者呢?
與此同時,北方的諸侯正在密謀叛亂,亨利四世治下的倫敦盜匪橫行,第二幕客棧的一幕,其中的情節可能也是莎士比亞的親身經歷,而盜匪和旅館老闆藉著聊天,也不忘諷刺當時的時政:
那些達官貴人,他們都是很有涵養工夫的,未曾開口就打人,不等喝酒就談天,沒有禱告就喝酒;可是我說錯了,他們時時刻刻都在為國家人民祈禱,雖然一方面他們卻把國家人民放在腳底下踩,就像是他們的靴子一般。
這就是造就福斯塔夫的時代背景。達官貴人並無榮譽可言,他們不承擔責任,只享受特權。
福斯塔夫的缺點一籮筐,罪行也不少,當他參與搶劫的時候,簡直是一齣荒誕喜劇,他走不動山路,一步一喘氣,還罵不停口。看在王子眼裡,「福斯塔夫流著滿身的臭汗,一路上澆肥了那瘦瘠的土地,倘不是瞧著他太可笑了,我一定會憐憫他的。」但是一轉身,這個看似笨拙的胖漢卻告訴王子,他辛苦劫回來的一千鎊已經被其他盜匪搶走,至於盜匪有幾人?一時說是兩個,一時說是四個,然後變成了七個、九個,十一個。
但是作者似乎一心為他開脫:
他老了,這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情,他的白髮可以為他證明,可是恕我這麼說,誰要是說他是個放蕩的淫棍,那我是要全然否認的。如果喝幾杯攙糖的甜酒算是一件過失,願上帝拯救罪人!如果老年人尋歡作樂是一件罪惡,那麼我所認識的許多老人家都要下地獄了;如果胖子是應該被人憎惡的,那麼法老王的瘦牛才是應該被人喜愛的了。
這番開脫,或許不僅適用於福斯塔夫,當時在座的觀眾,包括作者本人都不例外。
接下來,王子需要為父親效力,保衛王位,他為福斯塔夫在軍中謀得了一個職位,但是這樣一個無恥之徒,他真的會為國王賣命嗎?
「我把官家的徵兵命令任意濫用。我已經把一百五十個兵士換到了三百多鎊錢。」因為他專門挑選那些有身家的人,譬如小地主的兒子;訂了婚的準新郎,吃慣了牛油塗麵包,為了逃避兵役,一個個都忙著交錢給他。
結果他的隊伍裡全是「不老實的僕人、小兄弟的小兒子、搗亂的酒保、失業的馬伕,這一類太平時世的蠹蟲病菌。我把這些東西蒐羅下來,代替那些出錢免役的人們。」以至於王子嘆息說,他從來沒見過這麼「可憐相的流氓」。
但福斯塔夫解釋:「像這樣的人也就行了;都是些炮灰,都是些炮灰;叫他們填填地坑,倒是再好沒有的。咄,朋友,人都是要死的,人都是要死的。」
圍繞福斯塔夫的對白,可能是莎士比亞寫過最滑稽的内容:諸如甚麼「你的收入很微薄,花費卻很可觀」,「只要給你的腳戴上鐐銬,就能把你的耳病醫好」,「每一根白髮,都提醒我生命無常,應該多吃吃喝喝」。
這些憤世嫉俗的牢騷,作者寫來得心應手,觀眾也應心有戚戚焉。
福斯塔夫代表的,在新興的商業社會之中,(低階的)貴族愈來愈邊緣化,他們無法獲得相應的榮譽,事實上也不想要,正如引言那段振振有詞的嘲諷,對於最高權力的統治者而言,可謂大逆不道:如果所謂的榮譽,或者其他甚麼「大義」,在普通人眼裡只是空氣,那麼統治的大部分法術也就失靈了。而福斯塔夫不遺餘力地點破真相:榮譽只能欺騙死者,人只要活著,就要面臨譏諷和毀謗,追求崇高的名聲,幾乎不可能。
商業社會的發達,必將導致權力的分散。莎士比亞劇中借用了亨利四世的時代,其實寫的是伊利沙伯一世時代,而他本人就是一個中產階級。
古代的君王和貴族,都是憑藉戰爭和軍功起家,但到了商業社會,庶民文化興起,人性的本能想避免戰爭,國王和其他貴族之間的衝突,再以榮譽作為招徠,已經不是很行得通。正如福斯塔夫使用徵兵令,所能找到幾乎都是最底層的游民,稍有家產的人,都情願用金錢代替兵役。只有那些想要一夜翻身的,才會寄希望於戰爭,在王權專制的年代,戰爭是統治者的豪賭,最終的得益者,可能只有君主一個人。
福斯塔夫選擇放浪形骸,蔑視這種為國王賣命而得來的榮譽,在伊利沙伯時代的英格蘭,應該有廣泛的共鳴。福斯塔夫毫不意外成為莎士比亞戲劇中最受歡迎的角色之一,以他為主角 spin off 就有莎士比亞自己的喜劇「溫莎的風流婦人」和後世威爾第的歌劇。即使他體型肥胖、品行無賴,但是他有獨立的人格,世俗的智慧,他能看穿權力的把戲,在戰爭中,平民只有做炮灰的命,「勇氣的精要在於謹慎,唯此我才保住了性命」。(The better part of valor is discretion, in the which better part I have saved my life.)
當然,福斯塔夫的這種「敗壞」,也引起後世的不少批評,甚至批評到莎士比亞本人的品格問題,認為他沒有甚麼信仰和道德原則,但是誰又能否認,福斯塔夫說出了絕大多數普通人的心聲?至於莎士比亞是否認同他,並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