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1950 年代早期起,從莎士比亞創作生涯的開始一直到終結,他不遺餘力反覆探索一個讓人深深困惑的問題:怎麼可能會有一整個國家落入一個暴君手中的情形出現?」開宗明義發此斷論,「暴君:莎士比亞論政治」(Tyrant: Shakespeare on Politics)一書的說服力並非源自新歷史主義的理論,亦無涉作者文評家葛林布萊(Steven Greenblatt)的莎士比亞研究權威,而是對莎劇暴君的生動描述,梳理出其特質及上位條件 —— 譬如「理察三世」(Richard III)。
葛林布萊認為,莎劇中的理察三世之所以能得逞篡位,除了「事關人品」(a matter of character),更有賴於一眾「助紂為虐者」(enablers)。葛林布萊力數理察三世種種暴君特徵:
無邊自大,違法亂紀,樂於製造痛苦,有著宰制他人的衝動性欲望。這種人病態自戀和無比狂妄。他有一種肥大的權力意識,從不懷疑自己有權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痛恨法律是因為法律會擋他的路,也是因為法律代表的公共利益觀念為他所鄙視…… 他是個惡霸。他輕易就會勃然大怒,痛擊擋在他路上的任何人。
莎士比亞明確指出,理察三世天生怪相(「口吐毒液的駝背蟾蜍」;「畸形,醜陋,尚未完成一半即被提前送到人世」),被眾人甚至母親嫌棄(「你來人世我到地獄」),釀成心理扭曲,繼而促進其政治野心:「我在世上既無歡樂,唯有凌駕容貌勝我之人,我要將幸福寄託於皇冠之夢。」(Then, since this earth affords no joy to me, / But to command, to cheque, to o’erbear such / As are of better person than myself, / I’ll make my heaven to dream upon the crown)葛林布萊表示,早年母愛欠奉,因其外表常被眾人嘲弄,成年又缺乏性生活,對理察三世的自我形象造成永久創傷,表面上毫不在乎,但從他下令奏樂蓋過母親咒罵的舉動,證明多少有所觸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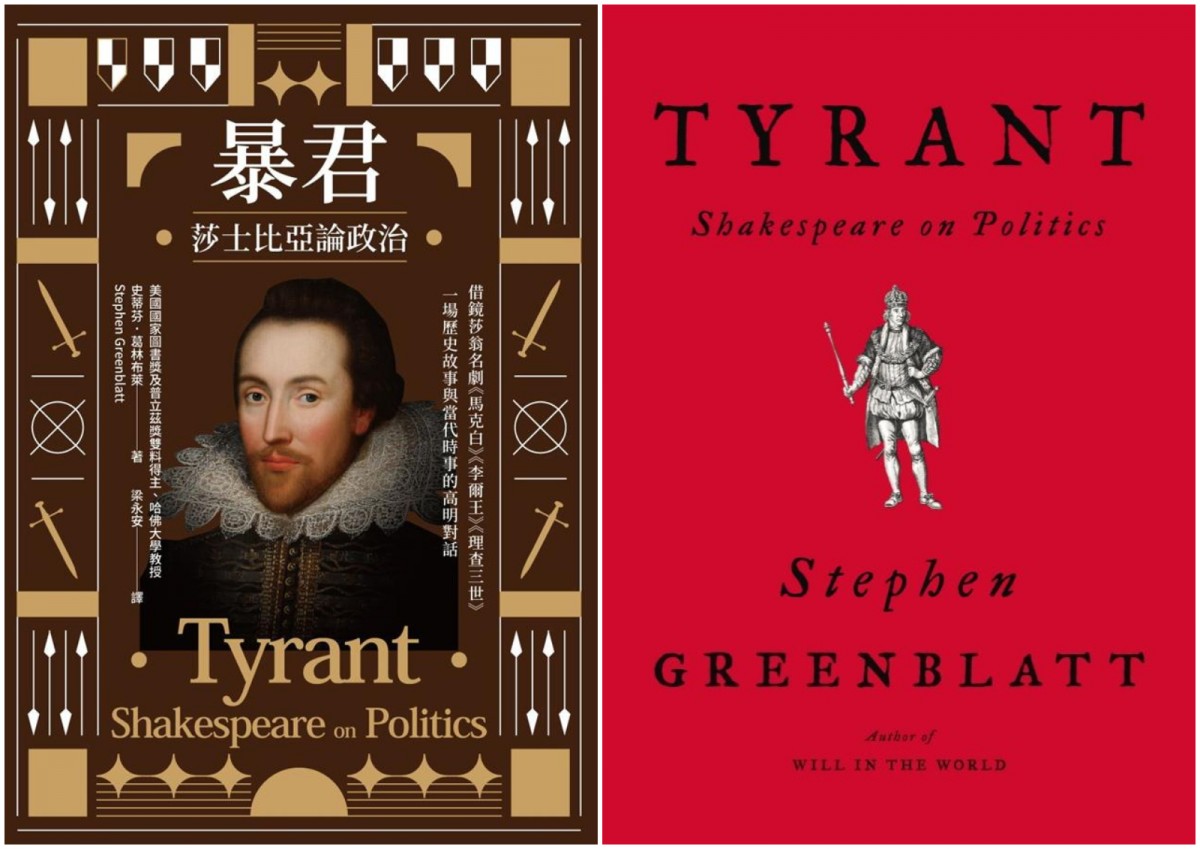
同一時間,理察三世亦體現出一種「莎士比亞認為是暴君最獨特的特徵」:將自己深印於他人心中,不管對象是否樂意。「就好像為了補償自己承受的痛苦似的,他找到一個方法(用暴力或欺騙)讓自己無所不在,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頭。沒有人可以無視他的存在。」連父親及丈夫均被理察三世謀害的安妮(Lady Anne)亦不禁對他產生好奇,一邊鄙夷,一邊自揣:「我倒是很想看看你這顆心。」最後更收下理察的求婚戒指。
葛林布萊對安妮的表現有一套獨到的解釋:古怪好奇心。「這齣戲並不鼓勵觀眾對理察的政治目標產生認同,卻會讓他們很高興看見有人代替他們釋放出壓抑的侵略性,以及敢於公然說出不容說出的話…… 理察不只邀請我們分享他愉快的桀驁不馴,還邀請我們體驗 —— 屈服於我們所憎厭的東西是甚麼感覺。」這種矛盾心理,正是理察三世既醜陋又吸引的基礎。

布坎南(George Buchanan)有言:國王統治自願的臣民,暴君統治非自願的臣民。莎士比亞卻屢屢表明,除了弔詭的魅力,暴君要成事還須爪牙協助,多方共謀;而當暴君要人執行惡法,恰如哈姆雷特所講,總會有「自己熱心求來差事的人」。就「理察三世」一劇,葛林布萊便歸納出最少六種助紂為虐者的特徵:
- 受蒙騙:天真無知,誤信理察謊言(二哥喬治/克萊倫斯公爵)。座右銘是「我不能想像」(喬治之子)。
- 被恐嚇:恫嚇於理察威迫:「不服從就變死屍。」自覺無能為力又或事不關己(倫敦塔衛隊長)。
- 合理化:善忘人士。明知理察是病態騙徒,仍然傾向將不合理現象正常化(對「理查萬歲」高呼阿們的市民)。
- 僥倖心:盲目樂觀。清楚理察行事劣跡,卻相信天下會繼續太平(海司丁斯勳爵)。
- 惡勢力:理察走狗,只問利益。以為同謀可免遭毒手,最後被逐一清算(白金漢公爵)。
- 執行方:打手配合。有怕麻煩(倫敦市長),有求好處(刺客),亦有純粹整人成癖。
「暴君的勝利奠基於謊言、虛偽的承諾,以及用暴力手段消滅對手。」同一套奪權方法卻不能用於治國。理察三世上台之後,眾叛親離,餘下班子不是離心離德就是裡通外敵(凱茨比),根本無力管治。而為鞏固毫無合法性的權力,又必須繼續犯罪,進一步加劇政權的合法性危機。「暴君統治具有倒轉權威的整個結構的效果:正當性不再寄託於國家的中心,而是授予了遭其暴力所侵害的人。」在莎士比亞的世界,暴君最終都會覆亡,無一例外。
「莎士比亞戲劇中幾乎沒有哪個角色不曾做出道德妥協。」此一觀察是否意味權力遊戲總是爾虞我詐,改朝換代不過以暴易暴,逞強一方永遠橫行?莎士比亞似乎並不認同。莎劇不乏忤逆暴君的人物 ——「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的寶麗娜(Paulina)、「大將軍寇流蘭」(Coriolanus)的護民官、「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的布魯圖(Brutus)、「李爾王」(King Lear)的肯特伯爵(Earl of Kent)—— 葛林布萊卻特別提到「李爾王」中一位家丁:康華爾公爵(Duke of Cornwall)俘虜葛羅斯特伯爵(Earl of Gloucester)後逼供不果,惱怒之下挖出他一隻眼。康華爾的家丁看不過眼,出言制止,主僕兩人繼而激烈纏鬥。最後家丁死於康華爾妻子劍下,康華爾後來亦傷重不治。葛林布萊評道:
莎士比亞不相信普通老百姓可以充當對抗暴政的堡壘。他認為他們太容易被口號擺佈、被威脅嚇到、被不值幾毛錢的禮物收買,不足以成為自由的可靠捍衛者。他筆下的暴君大部分都是被與他同一階級的成員反對和殺死。不過,「李爾王」裡那個無名無姓的家丁創造了一個可以象徵民眾反抗暴君的人物。這個人拒絕沉默和旁觀,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俯仰無愧。雖然有關他的描寫只有寥寥幾行字,他卻是莎士比亞筆下的大英雄之一。
願我們都有反抗暴政的道德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