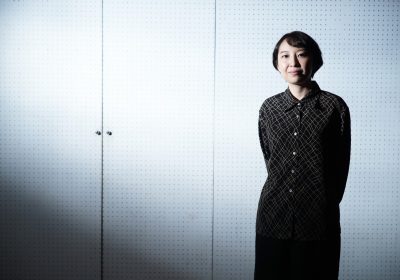香港導演張婉婷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本來好評如潮,更獲得第 29 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獎,但數日前爆出醜聞,原來被拍攝的學生們一直都以為只供校內播放,從來沒有同意以商業電影的形式公映,結果一星期內就宣佈下架。
有人認為當年本人和父母既然簽了同意書,今天就不能反口;或者是因為關於自己的片段比較負面,才搞出此等麻煩。大家必須認清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是次事件中,導演和學生是訪問者和受訪者的關係,不是僱傭關係,主角之一提供給媒體的同意書也證實了這點。學生沒有收取報酬,基於「紀錄片」的題材性質,事實上也不應該有酬勞。
在義務訪問的關係中,受訪者因甚麼理由而拒絕授權是毫不重要的,因為他本來就擁有在任何時間因任何理由退出的權利。沒有授權的訪問內容就不能夠使用,製作者花費了多少時間精力也不是考慮因素,這是訪問方法論中本來就存在的風險。
在學術制度中,任何研究計劃都需要通過倫理委員會的審查。嚴格而言,「需不需要通過審查」都是審查內容之一,所以即使你做的是文學文本分析,理論上都要向倫理委員會報告。審查最嚴密的當然是存在人類或動物生理實驗的醫學研究,其次是人類學和社會學等,進行社會訪問和觀察的調查,當中尤以涉及未成年對象的研究最嚴緊。
筆者讀研的第一學期已經需要修讀有關研究倫理的科目,其中一位分享者是醫療人類學的老師。她表示自己曾經有一個計劃是研究患者、患者家屬以及醫生護士的關係,但最後患者和患者家屬要脅研究者幫助他們爭取權益,否則不同意資料的使用授權,結果她 2 年間收集的資料完全白費。
以上不單是研究者的基本知識,在媒體傳播學中也是必修內容。如果是初出茅廬的製作者,犯錯或可以經驗不足推搪,以謝罪檢討作結,但以張導演的年資,這實在不是能夠簡單原諒的過失。加上這不是一時半刻的疏忽決定,而是長達 10 年間深思熟慮後的結果。事件發生後,網民翻出她過去種種劣行,由冒簽到無許可下進入比賽場地做訪問都有。在歷年的訪問中,本人直認不諱,對黑歷史毫無悔意,反認為是為拍攝成功的小聰明。
也許在差不多的國度中,為了主旋律而犧牲一兩束韭菜是符合國情的。但文明的制度裡,這是訪問倫理中,應當釘在恥辱柱上的反面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