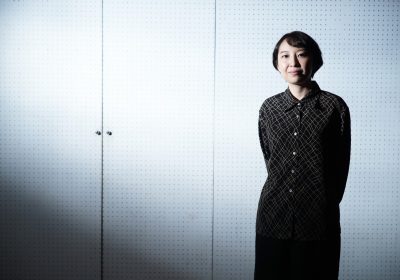杜林普數個月前在爭議聲中下台,自由派菁英歡呼喝采,一如既往嘲弄杜林普選民低學歷、鄉下佬。著名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卻在新書「才德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台譯:成功的反思)警告,才德至上的制度,使菁英階層恃才傲物,被全球化淘汰的勞工卻尊嚴掃地,積累的民怨成就杜林普上屆當選,但菁英階層始終不明白自己該負的責任,未能反省政治失敗的成因。

5 年前,杜林普成功登上總統寶座,華盛頓政壇一時措手不及,主流政黨和政治菁英才發現自己成為箭靶。投給杜林普的選民,主要都是勞動階層和傳統中產,沒有大專學歷的白人中,多達 3 分 2 投票給杜林普。他們在意伸張主權、國家認同與榮耀感,厭惡執政菁英和專業階層,批評他們借全球化自肥,將傳統產業外移中國等地,把勞動階級推落全球競爭的火坑,剝奪低下階層工作機會。究竟這股民怨是如何形成?
只要去試就能做到?
說實話,主流美國人向來都接受不平等與財富不均,因為他們相信一個人不論出身高低,只要憑藉才能與努力拚博,終有一日都有機會由貧轉富、向上流動,這是美國夢(American Dream)的核心精神。
戰後的美國經濟急速發展,確曾令無數美國夢得以成真,但踏入 21 世紀,向上流動的機會其實早就大不如前。入息組別最低 5% 的美國人,只有 4% 至 7% 可爬上入息最高 5% 階層,絕大多數連躋身中產都辦不到,顯示貧者愈來愈無法擺脫貧困命運,偏偏仍有多達 70% 美國人繼續堅信,窮人可靠自己脫貧。民主共和兩黨面對不平等的現況,標準回應亦依然是確保機會平等,前總統奧巴馬就最喜歡重彈「只要去試就能做到」(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的老調,就任總統期間公開說過不下 140 次。
當階級流動機會大減成為現實,但命運操之在己的美國夢信仰依然,兩者便調劑出一劑社會毒藥 —— 贏家自以為成功全憑自身才能和努力,無視個人運氣與社會因素,以致於恃才傲物;輸家則相信無法翻身都是自找,以致無止境的自我懷疑,因喪失社會貢獻而尊嚴受損。

雖然杜林普自身是億萬富豪,但相當了解這種輸家的屈辱心態,懂得在選戰中加以運用致勝。有別於三句不離「機會」的奧巴馬和希拉莉,杜林普絕少說「機會」,反而經常大談贏家與輸家,他承諾帶領美國人擺脫屈辱、重振美國昔日的偉大,聽在很多勞動階層耳裡都心有戚戚焉。對這些每日努力掙扎才能免於滅頂的中下階層而言,希拉莉再三強調的向上流動則更像是奚落,而非許諾。
對低學歷人口的公然歧視
事實上,全球化正是窒礙階級流動的元兇,跨國菁英階層如魚得水,本地勞動階層薪資卻停滯不前。自由派菁英不是沒有察覺問題,但他們沒有改革經濟結構,反而視全球化為必然現象,只管以政策減輕對勞工衝擊,然後繼續奉行才德至上原則,叫勞工自我進修增值來適應。對很多勞動階層而言,這無疑「難聽過粗口」。
從 1990 年代開始,民主共和兩黨都迷信教育是解決問題的良方,克林頓和奧巴馬是這套信念的堅實信徒,奧巴馬提拔的官員更多是名校出身,比例近乎歷屆政府之最。奧巴馬又在公開演講中警惕,沒大專學歷而找到好工的時代遠去,如今美國勞工不但要面對國內競爭,「還要面對數十億來自北京、班加羅爾和莫斯科的外國人」挑戰,所以只有進修才有望在全球化時代脫穎而出,「沒有受良好教育,就很難找到糊口的工作」。

但現實中,全球經濟金融化與壟斷現象,往往才是工作朝不保夕的結構成因。再者,即使高等教育廣開門路,但擁有大專學歷的美國人,依然只佔總人口 3 分 1 左右。當政治菁英反覆強調,個人成敗取決於大專文憑,結果也變相暗示,沒有大專學歷的大多數國民,在全球化下遭逢困厄都是咎由自取,政府不負任何責任。這種菁英階層的自以為是,也加深社會對低學歷階層的偏見。
桑德爾提醒,政治菁英高調反對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同時,對低學歷人口的歧視卻異常猖獗,「比對其他弱勢社群的歧視還要明顯,至少更不避諱」。數年前有社會心理學研究就發現,在黑人、勞動階層、窮人、肥胖者和低學歷人口之中,大專學歷菁英最蔑視低學歷人士,說出來更是毫無歉意,甚至連低學歷受訪者也普遍自我歧視,足見才德思想的根深柢固。
如此迷信取得大專學歷,工作才有尊嚴,才有臉在社會立足,結果只是侵蝕美國民主生活,貶低不具大專學歷階層的社會貢獻,將多數勞動階層排除在議會外。這就難怪鄙視菁英的杜林普,能夠得到大批低學歷白人選民支持 —— 杜林普沒有叫他們考文憑,與來自北京的中國勞工直接競爭,反而承諾剎停全球化巨輪,把外移的產業帶返美國。2016 年杜林普勝出共和黨初選時,甚至毫不避諱公開說道:「我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I love the poorly educated!)
重建生產者的社會尊嚴
事實證明,不論提高勞動階層的購買力、加強社會安全網,都不足以化解他們的忿恨和不滿,全因民怨來自社會認可和尊嚴的喪失,癥結可能在於主流的經濟觀念。如今的經濟政策都偏重消費者角色,結果只管補貼失業勞工的消費能力,為他們提供所需產品與服務,以為足以彌補他們的損失;但如果從公民角度著想,一個人最重要的經濟角色其實不是消費者,而是能夠貢獻社會的生產者。

桑德爾指出,我們從來都是以生產者的身份發揮個人潛能,透過滿足他人需要、擁有貢獻的機會,從而贏得社會尊嚴,這不能用薪資和金錢衡量。這種理念不流行於主流經濟學,卻早見於道德和政治傳統,亞里士多德便主張,人需要培養和發揮個人才能,方能自我實現(human flourishing)。傳統共和黨觀念都認為,從事農業、工藝和各種自由勞動,有利培養公民自治的德性,只不過此生產者倫理到 20 世紀逐漸消逝,被現今消費主義自由觀取而代之。
回歸根本,其實「美國夢」也提供了所需答案。桑德爾指出,作家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最先於 1933 年著作「美國史詩」(The Epic of America)提出美國夢,他頌讚美國為「賜予人類獨一無二的禮物」,土地上的男男女女,不論出身與地位,都有條件充分實現天賦潛能,以過得更好、更富裕、更圓滿,一切機會就取決於個人能力與成就。
但亞當斯的美國夢,不僅是向上流動的美夢,還是更整全的民主平等許諾,其筆下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正是這種精神的重要顯現 —— 館內累積上萬冊藏書,是美國人集體累積的公共資源,開放予公民自由取閱學習,不論男女老幼、黑白貧富、老闆工人、官員平民、教授學生,都可具備公共智慧活用這些知識。亞當斯堅信,只要這種民主平等的條件「在國民生活所有層面得以實現」,美國夢方可「長存不滅」。